狂欢过后,“赛博判官”机制还需见到实效
|
成林在北京经营着一家餐饮店。今年上半年,他卖出的一份外送牛肉河粉收到了一条让他感到莫名其妙的差评。“客人给了‘一星’,留言是‘米粉怎么是卤肉’。”实在想不明白客人想表达什么的成林,在外卖平台点击了“申诉”按钮,说明食物包含哪些食材、哪些调料,外卖如何打包等,把能解释的话说了个遍,希望能消除差评。 这条申诉没有像往常一样,由系统直接通过或驳回,而是被推给了外卖平台上的大众评审。两天过后,外卖平台给成林发送消息:投票结果显示,有20位大众评审员对这条评价投票,其中16人支持商家,4人支持顾客,成林的申诉成功了。 “赛博判官”或成网络经济管理创新方式 外卖平台App给作为店主的成林展示的评审机制显示,大众评审团主要致力于帮助解决有争议的评价,平台会把用户评价、商家回评、用户订单、用户备注、配送信息等内容推送给大众评审,评审以投票的方式决定支持用户或者商家。 评审机制还显示,在“评价与下单商品不符”和“用户未备注产生差评”的情况下,平台会为买卖双方发起大众评审。不过,经历了一次大众评审后,成林希望当系统直接驳回他的申诉时,他能再多一次申请大众评审裁决的机会。 之所以有这样的诉求,成林表示:“现在商家真的很被动。”几乎每次遇到差评,成林都会申诉,但能通过的只占少数,被驳回的那些申诉,大部分是由系统直接判定的,没有机会上大众评审。“如果系统直接驳回了申诉,就没有机会再重复上诉了,那条差评就永久地留下了。” 即使有时申诉成功了,成林还是一肚子委屈。有一次,一位点了外卖的顾客反馈,他备注了“要黄灯笼辣椒酱”,但收到的外卖里根本没有。成林私信客人,表示不是忽视备注,而是店里本身没有黄灯笼辣酱,所以才没有提供。让他没想到的是,他不解释倒还好,一解释客人更生气了,直接给了差评,说商家态度恶劣。“客人一不开心就给个差评,我们也没招儿,商家只能是错的一方,也不敢反驳,不然客人可能就更生气了。如果有的客人想撒气,还会去其他平台差评,商家更难以承受。”在成林看来,如果能多一次上大众评审的机会,商家获得客观评价的机会也就更大,如果不是商家的问题,就有机会消除差评,“如果大家觉得是商家的问题,那就该上差评上差评,商家该改进就改进”。 大众评审机制近年来被不少平台采用,不仅是成林所使用的外卖平台,抖音、微博等内容平台,也会邀请平台用户评判弹幕、博文等是否合规,一些二手交易平台也引入相关机制,由大众评审来评判交易纠纷中究竟孰是孰非。 在北京一所高校读书的李航就曾在二手交易中遇到过纠纷,并被平台安排了大众评审裁决。他卖出的是自己穿着大小不太合适的衣服,并提前和买家沟通好了衣服的情况,买家收到后,却表示要退货,原因是“不喜欢、不想要了”。李航没有同意退货,于是交易被交由大众评审判决。“双方上传了说明和凭据后,大众评审判我取胜,没有让对方退货。”李航说。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李长安认为,一些平台引入大众评审机制,纠正了过去平台经济当中单方面由消费者对商户进行评价的机制。“以往的评价机制中,消费者有了对商家进行评价的平台,但有些评价是否客观、合理有待商榷,商家提出反驳的权利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商家也是平台经济中的弱势群体。而平台引入‘赛博判官’,则给了商家一个为自己辩护的机会。” 做“判官”而非“看官”,大众评审机制仍需完善 尽管尝到了大众评审参与评判纠纷的甜头,李航还是觉得,一些平台的大众评审机制并不完善。“大众评审员的选择很随意,我也曾经被二手平台邀请担任过评审员,感觉评判的纠纷没有什么规律。裁判的规则是票数超过半数的一方胜利,一方只要比另一方多一票,就会被判胜,这并不合理。”另外他发现,交易双方举证的环节还没有结束,已经有大众评审开始投票了,这就意味着很多评审连证据都没看完就作出了“判决”,难免失之偏颇。 正如李航所担忧的,如今在社交网络上,既有人当“赛博判官”当得不亦乐乎,也有人被“赛博判官”“审判”得垂头丧气,甚至怒火中烧。一个网名为“momo”的用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,自己在某二手平台接受大众评审评判,开审时自己正在洗澡,还没来得及上传凭证,评审员们就听对方的一面之词,把票都投给了对方。一个名叫“香菜”的网友称,自己在二手平台上花200多元购入了一件衣服,收到后发现衣服不仅有很多污渍,还有异味,要求退货后卖家不同意,但愿意退款40元作为干洗费。这场评判中“香菜”以5∶9的票数告负,这样的结果令其很不满意。 根据自己的使用体验,李航认为平台可以给交易双方至少两轮说明和举证的机会,第一次自证其说,第二次回应对方的质疑,在这些举证环节结束后,再开启大众评审。“我此前还曾被微博邀请为评审,评判被举报的博文是否含有违规内容,平台会给出一些选项,让我选择博文是否有广告营销、人身攻击之嫌等。和一段文字或视频内容相比,买卖交易的情况更为复杂,评审员可能更难判断,平台或许也可以给一些帮助评审员判断的引导。” 刘季川常在二手平台购物,被邀请为大众评审。他曾被邀请评判的一起交易纠纷中,交易产品是电脑主板,买卖双方对产品的配置和性能各执一词,但作为外行,刘季川对其中的门道一知半解,只能“凭感觉”作出判断。 针对买卖双方及大众评审员遇到的问题,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苗鸣宇建议:平台一方面需要加强交易流程的数字证据保存和提供能力,加强员工培训,训练专门的争议解决客服机器人,结合不同类型的交易和服务,更好地指导争议双方保留和提交相关证据,便于评审员更好地作出理性判断。另一方面,平台应当通过后台算法和非隐私个人数据,建立完善的评审员评级制度,根据责任心、判断力等多种因素,对评审员进行评级。然后,将复杂程度不同的争议案件,分配给相应等级的评审员进行评审,以让“网络评审”的机制起到更多实效,帮助平台真正解决问题。 刘季川使用二手平台购物的一则经验是,如果不想被大众判官裁决,可以终止大众评审判决,申请平台客服裁决,“在我看来客服评判会比大众评审的评判更合理一些”。但李航曾经遇到过被大众判官判负后,想再向平台申诉,却被平台客服告知“结果只能是这样,请多体谅”。 不过,作为二手平台买家的大学生闫瑞瑞曾有过被大众评审判负后,向平台申诉成功的经历。她购买了一款化妆品后,发现收到的货物和自己此前在专柜购买的同款产品质地完全不同,和卖家沟通无果后,纠纷被交给大众评审。谁知刚进入评审流程,卖家就在举证的聊天框里疯狂刷留言,把闫瑞瑞提交的举证说明全都顶了下去。“大众评审员们可能只看到卖家提供的证词,我的说明很难被看到,随后我就在大众评审团那里‘败诉’了。” 由于不认可裁决结果,闫瑞瑞又向平台客服提出了申诉,指出了产品的问题,以及卖家在大众评审面前刷屏的情况。客服再次和卖家协商后,同意了闫瑞瑞的申诉,允许她退货退款。“不久以后,我发现那个售卖假化妆品的卖家被平台封号了,可能是也遭遇了其他人投诉的缘故。” 对于网络平台用户遇到的种种问题,李长安表示,并非所有商品都适合聘请“赛博判官”进行纠纷的评判,平台及其用户在引入和使用“赛博判官”这个机制时,也不要忘了其他的监督举措,如平台本身的监督,以及工商部门监督、专业评审机构的鉴定、消费者维权机构的权益保护等,这些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评判体系,帮助用户更好地解决问题。 苗鸣宇介绍,消费者有权对商家的商品和服务作出自己的评价,同时,商家也有维护自己商誉不受诋毁和歪曲的权利。消费者提出差评后,在差评的异议和评审阶段,商家作出一定的回应也是必要的。但双方行使自己权利并不能超过必要限度。如果消费者严重歪曲事实,或者同行恶意差评,用捏造的事实、侮辱性的言辞对商家进行不实评价,商家可以提起诉讼,要求该消费者删除不实评价,并赔礼道歉、消除影响;如果商家通过电话骚扰,邮寄污物等恶劣方式来骚扰差评消费者,也会受到治安管理处罚等制裁,“有偿删评”等还可能构成犯罪。 李长安还指出,“赛博判官”并非专业性质的审判员,对商品和服务质量的评判存在不专业的情况,甚至还有一些带有感情色彩。因此需要有相应的机制,让“赛博判官”的“判词”更为客观理性。要做到这一点,“赛博判官”的选择需要有一定的标准,可以请相关监管部门及专业人士来参与制定筛选机制;平台也可以为“赛博判官”制定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,让“赛博判官”群体既有准入门槛,又能流动起来,有进有出。 “‘赛博判官’作为第三方力量介入到网络经济的评价过程中,弥补了传统评价体系的缺陷,有利于平衡各方的利益,是网络经济管理机制体制的一项创新。当然,‘赛博判官’模式刚推出时间不长,其实际效果仍有待市场检验。而这些评审人员的选择机制、评价标准等如何确立,也是其能否持续发展下去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。”李长安说。 (应受访者要求,文中成林、刘季川、李航、闫瑞瑞为化名) 中青报 责任编辑:共工社 |
头条阅读
最热资讯
精彩推荐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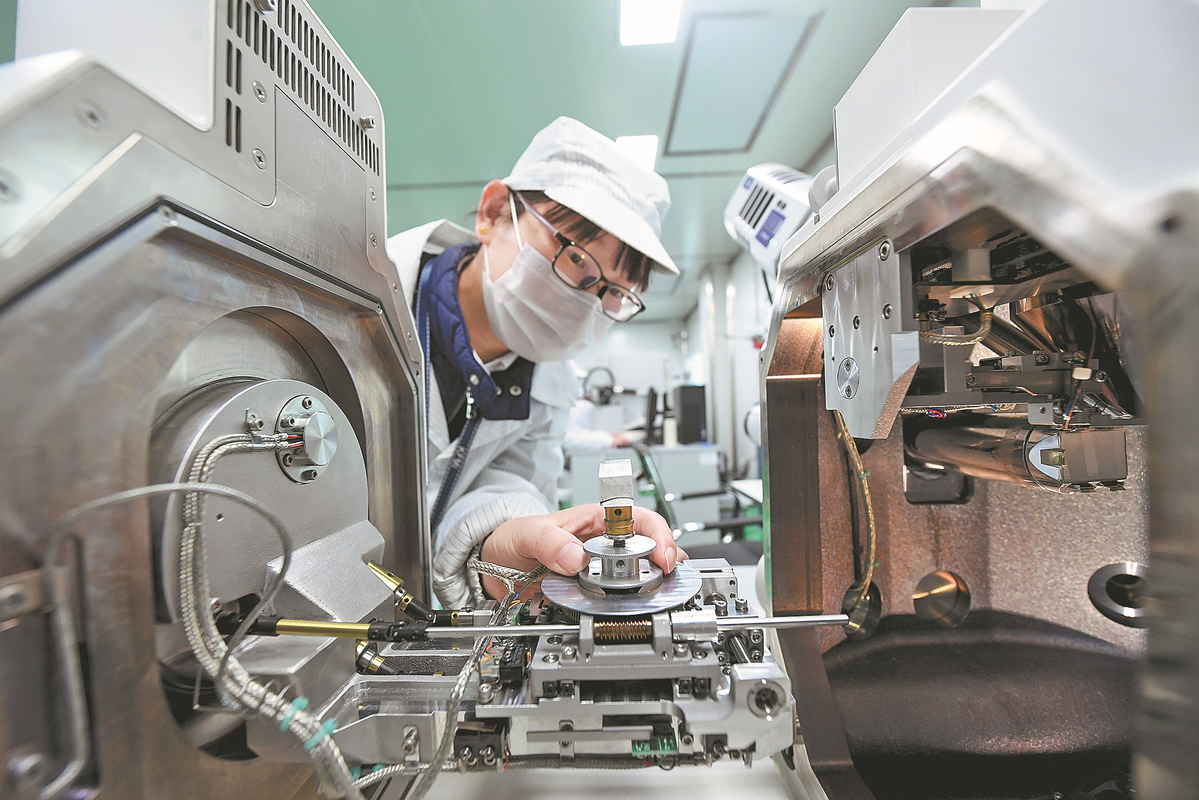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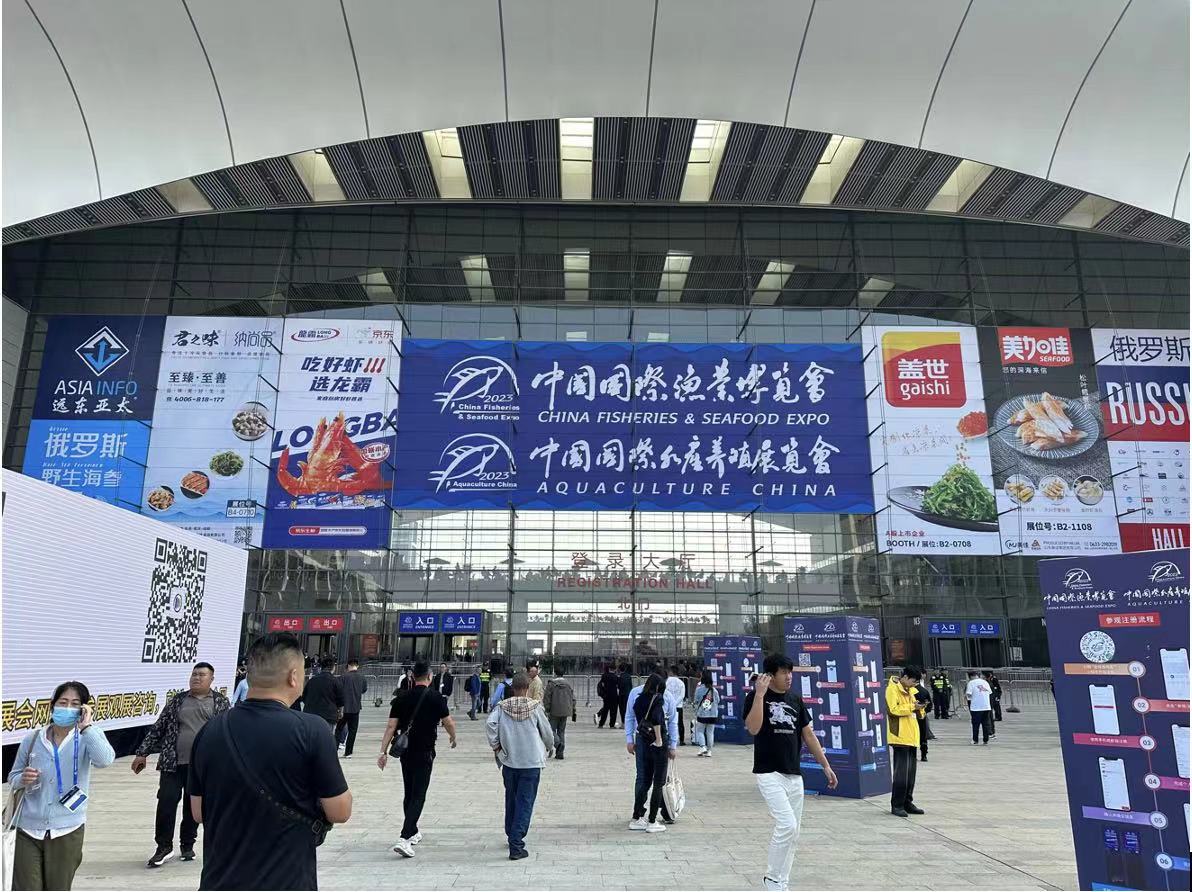


 海报分享
海报分享